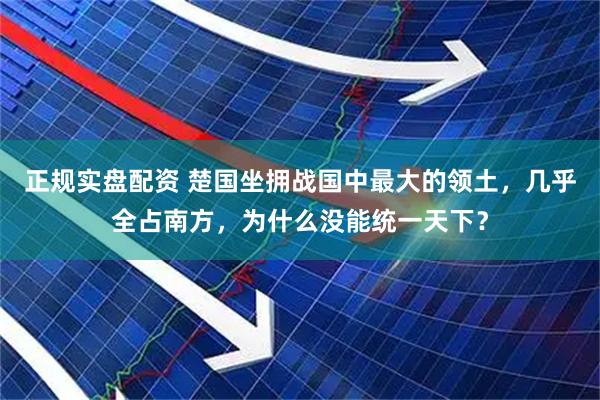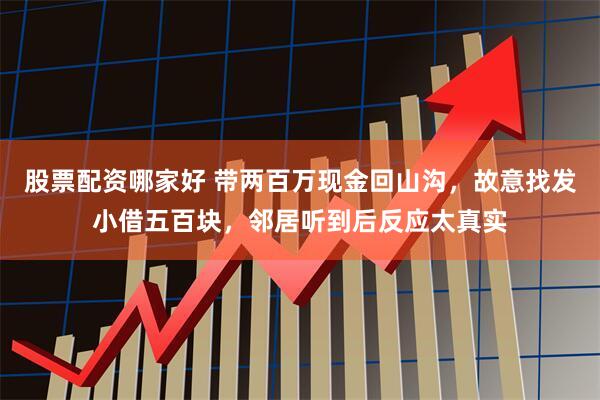
“哎,二雷子,你瞧见没?刚才村口那辆过路的大巴车上下来的好像是林冬?”
“哪个林冬?老林家那个去省城赚大钱的小子?”
“可不就是他!但我看怎么不像赚了大钱的样子啊。穿着件都要掉色的旧夹克,胡子拉碴的,手里还提着个尿素袋子,那袋子上缠满了胶带,看着跟逃荒似的。”
“真的假的?前两年不还传他当了大包工头,还要回村盖别墅吗?”
“快拉倒吧!刚才他在小卖部买烟,我就在旁边。你猜怎么着?他盯着那软中华看了半天,最后买了包五块钱的红梅。我看呐,这是在外面工程烂尾,赔了个底掉,没脸见人,偷偷溜回来躲债的。”
“啧啧,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隔壁刘三欠他家那笔烂账,估计更要不回来了。你看这世道,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。”
01
深秋的夜,雨下得有些凄厉。风像是有了灵性,专门往人的骨头缝里钻。
一辆满身黄泥、显得疲惫不堪的长途客车,“吭哧”一声停在了青石沟村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。车门打开,售票员不耐烦地催促了一声,一道黑影略显狼狈地钻进了雨幕里。
展开剩余96%林冬站在村口的烂泥地上,脚下的解放鞋瞬间就被冰冷的泥浆没过了脚面。他没有急着走,而是回身从车底的行李舱里,费力地拖出了一个巨大的编织袋。
那袋子原本是装复合肥用的,白色的袋皮已经泛黄,上面印着的红字模糊不清。袋口被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,鼓鼓囊囊的,棱角分明,看着就死沉。
林冬深吸了一口夹杂着湿土腥味和枯叶腐烂气息的空气,这就是家乡的味道。十年了,这味道似乎一点没变,苦涩中带着股让人清醒的凉意。他弯下腰,抓住编织袋的提手,猛地一发力。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暴起,那个袋子才极其沉重地离开了地面。
太沉了。
这里面装的不仅仅是他在省城建筑工地上,没日没夜吸着水泥灰、顶着大太阳换来的东西,更是他这十年憋在胸口的一口气。
他把袋子扛上肩头,沉重的分量压得他那一米八的汉子也不由得把腰弯成了虾米。雨水顺着他乱糟糟的头发流进脖子里,冰凉刺骨,但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,却烧着一团火。
路过村口那家亮着昏黄灯光的小卖部时,里面的热闹声传了出来。几个村里的闲汉正围着炉子打牌,烟雾缭绕。
林冬不想引人注意,但这身行头实在太扎眼。
“哟!这不是冬子吗?”眼尖的二雷子隔着沾满水汽的窗玻璃喊了一嗓子,紧接着推开门,一股热浪夹杂着廉价烟草味扑了出来,“怎么着,大老板回乡省亲,连个专车都没有,坐过路大巴回来的?”
这一嗓子,把屋里几个人的目光都勾了出来。
林冬停下脚步,把肩上的袋子往上颠了颠,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,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:“雷哥说笑了,啥大老板啊,也就是在外面混口饭吃。这不,今年行情不好,没混下去,回来歇歇。”
“混不下去?”二雷子吐了口烟圈,目光在那个破编织袋上扫了几个来回,眼神里的戏谑更浓了,“听说你在省城包大工程,怎么回来连个拉杆箱都不舍得买?这里面装的啥?旧铺盖卷啊?”
周围响起了一阵哄笑声。那是看客们特有的、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。在青石沟,只有两种人最能成为谈资:一种是飞黄腾达的,一种是摔得鼻青脸肿的。显然,此刻的林冬在他们眼里属于后者。
林冬没有反驳,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,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,转身走进了黑暗的雨巷。
身后传来的议论声,顺着风钻进他的耳朵。
“看见没?那怂样,绝对是破产了。”
“估计是欠了一屁股债,回来避风头的。”
“哎,老林头要是活着,看见儿子这德行,估计得再气死一回。”
听到“老林头”三个字,林冬扛着袋子的手猛地攥紧,指节发白。他咬着牙,没有回头,只是脚下的步子迈得更沉重了,每一步都在泥地里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。
回到那座荒废了三年的老屋,院子里荒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。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,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“吱呀”声,仿佛是老屋在哀鸣。
屋里一股霉味。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亮,能看到桌椅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。
林冬没有开灯,他摸索着把那个死沉的编织袋塞进了里屋那张旧架子床的深处,又找了几块破砖头和烂纸箱挡在外面。做完这一切,他才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,瘫坐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他从怀里掏出那包刚买的红梅烟,哆哆嗦嗦地点上一根。火光忽明忽灭,照亮了他那张沧桑却棱角分明的脸。
他看着床底下,喃喃自语:“爹,我回来了。有些账,该算了。”
02
这一夜,林冬睡得很不踏实。梦里全是父亲临终前那张灰败的脸,还有工地上轰鸣的搅拌机声。
第二天醒来,雨停了,天色依旧阴沉得像一口倒扣的破铁锅。
林冬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,虽然还是很破败,但好歹有了点人气。快晌午的时候,他从兜里摸出仅剩的一张百元大钞,去村头肉铺割了半斤猪头肉,又去小卖部打了一瓶最便宜的散装二锅头。
提着这些东西,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村东头的发小王大柱家。
王大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。三间土坯房因为年久失修,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,露出了里面的草泥。院墙塌了一半,用几根树枝胡乱挡着。
刚走到院门口,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那是大柱媳妇,常年犯喘病,是个药罐子,也是拖垮这个家的主要原因。
“大柱在家不?”林冬喊了一嗓子。
门帘一掀,一个黑瘦黑瘦的汉子走了出来。王大柱才三十四岁,背却有些驼了,脸上全是像树皮一样粗糙的皱纹,手上的裂口里嵌满了洗不掉的黑泥。
一看是林冬,王大柱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,像是点燃了两盏灯。
“冬子!你啥时候回来的?咋不提前说一声,我好去接你啊!”大柱快步迎上来,也不嫌林冬身上那件脏兮兮的夹克,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,那是实打实的热情。
“昨晚回来的,太晚了就没惊动大家。”林冬笑着扬了扬手里的酒肉,“想着好久没跟你喝两盅了,这不过来蹭个饭。”
“快进屋!快进屋!”大柱把林冬让进屋里。
屋里光线很暗,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,只有一张缺了一条腿、用砖头垫着的方桌。墙角堆着些杂物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和潮湿的霉味。
大柱媳妇挣扎着要从炕上起来打招呼,被林冬赶紧拦下了:“嫂子你躺着,别动,都是自家人客气啥。”
两人在桌边坐下,大柱拿来两个缺了口的酒碗,倒满酒。
几杯酒下肚,话匣子也就打开了。大柱问起林冬在外面的情况,林冬叹了口气,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苦涩无比。
“大柱,实不相瞒,这次回来,我是实在没地儿去了。”林冬低下头,声音低沉,带着一股走投无路的悲凉,“外面的工程本来做得好好的,结果大老板卷钱跑了,卷走了几个亿。我垫进去的材料费、人工费,全打了水漂。现在不仅没赚到钱,还欠了材料商一屁股债,连回来的路费都是跟工友凑的。”
王大柱端着酒碗的手僵在了半空,愣愣地看着林冬:“这么……这么严重?那你以后咋办?”
“还能咋办,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林冬搓了一把脸,显得无比颓废,“我现在连个落脚的地儿都难。老屋那房顶漏得厉害,昨晚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,被窝都是湿的。兄弟,你看你手头方便不?能不能借我五百块钱?我想买点瓦和油毡,先把房顶修修,好歹能住人。”
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五百块。
对于十年前的林冬来说,那是一顿饭钱。对于现在的城里人来说,可能也就是件衣服钱。可对于王大柱这个家来说,那是救命的钱,是全家人两个月的口粮。
林冬偷偷观察着大柱的反应。他在赌,赌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种东西叫情义,赌这十年的人心有没有彻底变凉。
王大柱没有说话,也没有犹豫。他放下酒碗,站起身,转身就开始翻箱倒柜。
他先是从枕头底下的那个旧布包里摸出一把零钱,数了数,觉得不够。又蹲下身,从床底下的鞋盒子里翻出一叠皱皱巴巴的一块、五块的纸币。
最后,他走到那个窗台上放着的、用泥烧的存钱罐前,那是他给上小学的儿子存的。他咬了咬牙,拿起旁边的锤子,“哗啦”一声,把存钱罐砸了个粉碎。
硬币滚了一地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王大柱趴在地上,一个一个地把硬币捡起来,不管是五毛的还是一毛的,都捡得干干净净。
他把所有的钱都堆在桌上,那是一堆花花绿绿、甚至带着汗味和泥土味的钱。
“冬子,这里一共是五百二十块三毛。”王大柱把钱推到林冬面前,脸上带着憨厚甚至有些愧疚的笑容,“家里就这么多现钱了。原本是打算给娃交下学期书本费和给你嫂子买药的。你先拿去救急,修房子要紧,别淋坏了身子。至于药……我再想办法去山里挖点草药顶一顶。”
林冬看着那堆钱,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堵住了,酸涩得厉害。他的视线有些模糊,那哪里是钱,那是大柱的心,是这世道里最干净、最滚烫的东西。
他这十年在外面,见过为了几万块钱亲兄弟反目的,见过为了利益背后捅刀子的,见过酒桌上称兄道弟转头就落井下石的。可在这个穷得掉渣的山沟里,这个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发小,为了他一句谎话,砸了儿子的存钱罐。
“大柱,这钱……我要是拿了,嫂子的药咋办?”林冬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“拿着!”王大柱把钱硬塞进林冬手里,语气坚定,“咱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你有难,我要是干看着,那还是人吗?钱没了再挣,人好好的就行。你放心,只要有我一口干的,就绝不让你喝稀的。”
林冬紧紧攥着那把零钱,指甲掐进了肉里。这五百二十块钱,比他床底下那个装了两百万的编织袋还要重,重得压得他心口生疼,也暖得让他想流泪。
03
在农村,消息比风跑得还快。
林冬“破产躲债、穷困潦倒、连修房顶的五百块都要找王大柱借”的消息,不到半天时间就传遍了青石沟的每一个角落。
村民们的反应各异,有叹息的,有嘲笑的,更多的是等着看笑话的。
这天下午,林冬正在院子里假装收拾杂草,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在院门口晃悠了半天,最后提着个黑色的塑料袋走了进来。
来人正是林冬的邻居,刘三。
提起这个刘三,林冬心里的火就压不住。三年前,林冬的父亲突发脑溢血,急需三万块钱做手术。当时林冬在国外的工地上,一时半会转不回钱来,就给刘三打电话,让他把当年借走的三万块钱还给父亲救命。
结果刘三在电话里哭穷,说自己做生意赔了,一分钱没有。一拖再拖,最后林冬的父亲因为没钱交手术费,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,撒手人寰。等林冬赶回来奔丧时,刘三连面都没露,说是去外地躲债去了。
这笔账,是林冬心里的刺,是血海深仇。
只见刘三穿着一件袖口都磨破了的旧军大衣,脚上的解放鞋还露着大脚趾头,头发乱得像鸡窝,一脸的愁苦相。一进门,他就先挤出了几滴眼泪。
“哎呀,冬子啊!听说你遭了大难了?叔这心里难受啊!”刘三把手里的黑塑料袋往地上一放,袋口散开,滚出来几个表皮发黑、甚至生了芽的烂红薯,“叔家里也没啥好东西,这几个红薯你留着烤了吃,别饿着。”
林冬冷眼看着刘三这副滑稽的表演,心里冷笑,脸上却不动声色,只是淡淡地说:“三叔来了,坐吧。”
刘三见林冬没赶他走,胆子大了起来,一屁股坐在那满是灰尘的门槛上,拍着大腿就开始哭穷,那演技,不去拿奥斯卡简直屈才。
“冬子,你也别怪叔这几年不还钱,也没露面。你是不知道,叔苦啊!”刘三抹了一把鼻涕,声音凄厉,“这几年做啥赔啥,家里养的猪瘟死了,地里的庄稼也被水淹了。这几年,我和你婶子连过年都不敢割肉,天天喝稀饭。别说三万了,现在你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卖了,我也拿不出三百块啊!”
说着,刘三哆哆嗦嗦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,硬塞到林冬手里,那手还在不停地抖:“这十块钱是你婶子攒了半个月鸡蛋换来的,你拿着买包盐。当年的账……等叔以后有钱了,一定还!就是砸锅卖铁也还!叔不能让你吃亏啊!”
林冬看着手里那张带着体温的十块钱,又看了看地上的烂红薯,再看看刘三那张写满了“真诚”的脸,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嘲讽。
“三叔,我爸当年的救命钱,你真的一分都没有?”林冬突然问了一句。
“真没有!要有我天打雷劈!不得好死!”刘三举起三根手指发誓,眼珠子骨碌碌乱转,眼泪说来就来,“我现在穷得都要去要饭了!冬子,咱们都是苦命人,以后咱们叔侄俩相依为命吧。”
送走了这位“影帝”,林冬脸上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,眼神冷冽得像冬夜的寒风。他反锁了院门,拉上了那条破烂的窗帘。
他走到床边,费力地把那个沉重的编织袋拖出来,伸手探到底层,在那些红色的砖头下面,摸出了一个密封的牛皮纸档案袋。
这是他回村前,花了大价钱请省城最专业的私家侦探调查的资料。
林冬深吸一口气,坐在昏暗的灯光下,缓缓绕开档案袋上的白线,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桌子上。
那不是钱,而是一叠高清照片和几张盖着公章的复印件。
看到照片上的内容后,林冬整个人僵在灯影里,瞳孔猛地收缩,照片上的画面让他震惊了,捏着照片的手指骨节发白,眼底涌起一股滔天的怒火。
照片上,那个刚才还在哭诉“连过年都不敢割肉”、“穷得要饭”的刘三,此刻正坐在县城最高档的“锦绣花园”小区的麻将馆里。
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衣,头发梳得油光锃亮,手腕上戴着一块金灿灿的手表,嘴里叼着中华烟。他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百元大钞,怀里还搂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,正笑得满脸红光,推着牌九。
那张脸上的得意与嚣张,与刚才在林冬面前的愁苦与卑微,简直判若两人。
照片右下角的时间显示,就在昨天下午!
而那张复印件更像是一把尖刀,狠狠扎进林冬的心窝——那是一份房产过户证明,户主写的是刘三儿子的名字,付款金额正是三万多块的首付,而付款日期,恰恰是三年前林父病重急需用钱的那几天!
原来,那是父亲的救命钱,却被这畜生拿去给儿子付了首付!
这哪里是欠债,这是人命!这是血债!
林冬的手颤抖着,将照片一张张收好,重新装进档案袋。既然你想演戏,既然你想把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,那咱们就陪你演到底。等到大幕拉开的那一刻,我看你怎么收场,看你怎么把你吐出来的那些话,再一个个吞回去。
04
第三天,原本平静的青石沟被一阵嘈杂声打破了。
一大早,村西头就传来哭喊声和打砸声。林冬正在院子里劈柴,听到动静,眉头一皱,丢下斧头就往外跑。
声音是从王大柱家传出来的。
还没进院子,就看见外面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,一个个伸长了脖子,指指点点,却没人敢上前。
院子里,一片狼藉。大柱媳妇熬药的砂锅被摔碎了,黑褐色的药汁流了一地。几只鸡被吓得满院子乱飞。
村里的恶霸赵彪,正带着三四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,站在院子中央。赵彪嘴里叼着根烟,手里拎着根用来打架的钢管,一脸的横肉随着他的吼叫一颤一颤的。
赵彪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放高利贷的,也是村里的土皇帝。谁要是惹了他,轻则家里鸡犬不宁,重则被打断手脚。
王大柱为了给媳妇治病,半年前实在没办法,借了赵彪一万块的高利贷。原本说好利息不高,结果利滚利,半年时间就滚到了两万。
“王大柱!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儿!要是再不还钱,我就把你家这几间破房扒了抵债!把你媳妇那几件破衣服扔出去!”赵彪一脚踹翻了大柱家那个唯一的板凳,指着瑟瑟发抖的王大柱骂道。
王大柱死死护着身后哭泣的媳妇,急得满头大汗,脸涨成了猪肝色:“彪哥,彪爷!再宽限几天,地里的麦子马上就收了,收了我就还……”
“宽限个屁!我都宽限你三个月了!”赵彪一口唾沫吐在地上,眼珠子一转,阴恻恻地笑了,“听说你那个发小林冬回来了?还借给你五百块钱?怎么着,你是不是指望那个穷光蛋替你还?”
人群里,刘三那个老赖也在。他抱着膀子站在最前面看笑话,脸上挂着那副招牌式的奸笑,时不时还阴阳怪气地插嘴:“哎呀大柱,你就别指望林冬了。他连修房顶的钱都是借的,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,哪有钱管你这烂摊子。我看呐,你还是赶紧把那头牛卖了吧,虽然也不值几个钱。”
林冬分开人群走了进去,正好听见这句话。他看了一眼刘三,刘三缩了缩脖子,躲开了林冬的目光。
此时,赵彪正让人去拉大柱家那头唯一的耕牛。那是大柱一家的命根子,没了牛,这地就没法种了。
“住手!”
林冬一声断喝,声音不大,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他几步走到大柱身前,挡住了赵彪的人。
“哟,这不是林大老板吗?”赵彪上下打量着林冬那一身旧衣服和沾满泥的鞋子,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嘲讽,“怎么,你要替这窝囊废出头?行啊,既然你要当英雄,那就拿钱来!两万块,少一个子儿都不行!”
林冬面无表情地看着赵彪,眼神平静得像一口深井:“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但这利息算得不对吧?一万块半年滚成两万,你这是抢劫,也是违法的。”
“违法?”赵彪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,夸张地大笑起来,“在青石沟,老子的话就是法!老子就是抢劫,你能怎么着?”
他把手里的钢管往掌心一拍,逼近林冬,那股带着烟臭味的口气喷在林冬脸上:“没钱就滚一边去,别溅你一身血!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,一个要饭回来的,还想充大头蒜?信不信老子连你一块收拾!”
05
赵彪的嚣张气焰点燃了全场,几个小混混也跟着起哄,推推搡搡要动手。周围的村民虽然同情大柱,但没人敢惹赵彪,只能发出一阵阵无奈的叹息。
王大柱急了,一把拉住林冬的胳膊,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:“冬子,你快走!这事跟你没关系,别连累你!我就这一条烂命,大不了跟他们拼了!”
林冬拍了拍大柱那双颤抖的手,给了他一个安定的眼神。然后他转过身,直视着赵彪,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:“两万是吧?行,我替他还。”
这话一出,全场先是一静,随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
笑声最大的是刘三,他捂着肚子,眼泪都笑出来了:“哎哟笑死我了,林冬你是不是喝假酒了?脑子坏掉了吧?你兜里那五百块还是找大柱借的,你拿什么还?拿嘴还啊?还是把你那几斤肉卖了?”
赵彪也乐了,指着林冬的鼻子,满脸的戏谑:“行!你有种!你要是能当场拿出两万,我赵彪喊你一声爷!你要是拿不出,今天我就打断你们俩的腿,让你爬着出这院子!”
“等着。”
林冬没有多废话,转身出了院子。众人都以为他是借机想溜,赵彪更是得意地让手下守住门口。
没两分钟,林冬又回来了。
只是这一次,他手里提着那个沾满泥巴、缠满胶带的破编织袋。他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走得很稳,那个袋子在他手里晃晃悠悠。
赵彪看着那个破袋子,不屑地撇撇嘴,一口浓痰吐在地上:“提一袋子破烂来抵债?你是想捡破烂抵账吗?还是里面装的是旧报纸?”
说着,他为了在众人面前立威,抬起脚,狠狠一脚踢向那个编织袋。
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
编织袋被踢翻在地,上面覆盖的几件旧棉袄和烂衣服散落一地,露出了下面那个鼓鼓囊囊、用塑料布包裹着的内衬。
林冬弯下腰,没有去捡那些衣服。他的动作很慢,慢得让人心慌。他伸出手,抓住了编织袋内衬的一角,手指猛地用力。
“刺啦——”
随着一声刺耳的裂帛声,那层劣质的编织袋和塑料布彻底裂开。袋子里的东西,像是决堤的洪水一样,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深秋正午那耀眼的阳光下。
所有人的笑声戛然而止,赵彪脸上的横肉剧烈颤抖,死死盯着地上的东西,看到那一抹刺眼的红色后彻底震惊了,连呼吸都仿佛凝固了一般。
那不是破烂,也不是棉絮,更不是旧报纸。
那是钱。
是真金白银的钱。
整整齐齐、一捆一捆的百元大钞,像红色的砖头一样码放在那里。足足有二十捆,两百万现金!在阳光的照耀下,那红色的光芒刺得人眼睛生疼,红得让人眩晕。
而在那堆钱的最上面,还放着一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。那是林冬这十年来,通过各种渠道,花重金搜集的,关于赵彪在这一带非法放贷、暴力催收、甚至涉及几起伤害案的所有账目和证据!
这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风停了,树叶不响了。王大柱张大了嘴巴,下巴差点掉在地上。刘三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,脸上的笑容僵死在脸上,像个活见鬼的小丑。赵彪手里的钢管“当啷”一声掉在了地上,砸在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那个刚才还被他们嘲笑是乞丐、穷光蛋的林冬,此刻站在那堆钱旁边,身姿挺拔如松,眼神锐利如鹰,浑身散发着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霸气。
06
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足足一分钟。只有几只不知趣的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。
林冬弯下腰,慢条斯理地从那堆钱里捡起两捆。他在手里掂了掂,那沉甸甸的分量,是力量,也是尊严。
他走到已经傻眼、浑身开始轻微颤抖的赵彪面前。
“啪!”
一声脆响。林冬把两捆钱重重地拍在赵彪的脸上。那力道之大,直接把赵彪打得一个踉跄,半边脸瞬间红肿起来。
赵彪被打蒙了,但他连个屁都不敢放,甚至不敢捂脸。
“这是两万。连本带利,还你的。”林冬的声音不高,却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威压,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赵彪的心坎上,“钱给你了,拿着钱,滚。”
赵彪看着林冬,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个黑色笔记本,冷汗顺着额头哗哗地往下流。
他是混社会的,最懂眼色,也最知道厉害。能随手拿出两百万现金放在编织袋里的人,绝对不是他能惹得起的。更可怕的是那个本子,林冬既然敢亮出来,就说明手里捏着他的命门。那个本子要是交上去,他这辈子就完了,得把牢底坐穿。
“是……是……林爷,我有眼不识泰山,我滚,我这就滚。”赵彪捡起地上的钱,手都在抖,点头哈腰,像条丧家之犬一样,带着几个小混混灰溜溜地跑了,连狠话都没敢留一句。
赵彪一走,院子里的气氛瞬间变了。
那些刚才还跟着嘲笑林冬的村民,此刻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,眼神里充满了敬畏、震惊,还有深深的讨好。
“我的妈呀,原来林冬真是大老板啊!”
“这两百万得多少钱啊?能盖多少房子啊!”
“这才是真人不露相啊,咱们都眼瞎了。”
就在这时,一直躲在人群后面,想趁乱溜走的刘三,被林冬叫住了。
“三哥,别急着走啊。”
林冬的声音不大,却像是一道定身符,把刘三钉在了原地。刘三的背影僵硬了一下,缓缓转过身,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林冬弯腰捡起地上的那个档案袋,一步步走向刘三。每走一步,刘三的脸色就白一分。
“刚才你说,你穷得连过年都不敢割肉?说你要是有钱,天打雷劈?说你和我婶子天天喝稀饭?”林冬站在刘三面前,把档案袋里的照片和房产证明一张张抽出来,高高举起,展示给周围的乡亲们看。
“来,大伙儿都看看。这就是咱们村最穷的刘三哥。县城一百平的大房子住着,麻将桌上几千几万的输赢,却欠着我爸的一条命不还!却看着我爸因为没钱做手术死在家里!”
07
照片在村民手中传递,像是一颗颗炸雷在人群中炸响。
“天呐!这真是刘三?穿得跟大老板似的,还搂着女人!”
“这房子真气派!写的是他儿子的名字!原来他这几年哭穷都是装的!”
“太缺德了!太不是东西了!拿着林冬爹的救命钱去买房,这还是人吗?”
“刘三,你良心让狗吃了!”
指责声、唾骂声像潮水一样涌向刘三。那些平日里被刘三骗过的村民,此刻更是愤怒不已。
刘三看着那些铁一般的证据,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他那张虚伪的面具,被林冬当着全村人的面,撕得粉碎,连渣都不剩。
那种被千夫所指的恐惧,让他彻底崩溃了。
“冬子……冬子我错了!我是畜生!我是王八蛋!我不是人!”
刘三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,对着林冬疯狂磕头,把额头都磕破了,鲜血直流。鼻涕眼泪糊了一脸,这次是真的哭了,是被吓哭的,也是被悔恨淹没的。
“你饶了我吧!看在邻居一场的份上,饶了我吧!钱我还!我现在就去卖房子还你!连利息我都还!”
林冬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丑态百出的小丑,眼中没有一丝怜悯,只有冰冷的审视。
“晚了。”
林冬掏出那部旧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。那是他回村前就已经联系好的县法院执行局的电话。其实早在半年前,他就已经在外面委托律师起诉了刘三,并且胜诉进入了执行阶段,只是刘三一直躲着找不到人,财产也转移了。
现在,证据确凿,人也在场。
“喂,王法官吗?我是申请执行人林冬。被执行人刘三找到了,他就在现场,而且我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,涉嫌转移财产和抗拒执行……对,就在青石沟,麻烦你们过来一趟。”
听到“法院”两个字,刘三两眼一翻,瘫软在地上,像一摊烂泥,裤裆里流出了一股腥臭的液体。他被吓尿了。
半小时后,警笛声响彻了青石沟。刘三被带上了警车,等待他的不仅是强制执行、变卖房产,还有拒不执行判决的拘留,甚至是刑事责任。
恶人自有恶人磨,但这一次,磨他的不是恶人,而是正义,是林冬隐忍十年磨出来的一把利剑。
08
尘埃落定。
老屋的院子里,人群散去。林冬把剩下的钱重新装回了那个破编织袋,随意地就像装了一袋土豆。
他从里面抽出十万块钱,递给了还在发愣、仿佛在做梦的王大柱。
“冬子,这……这我不能要!”王大柱像是被烫到了手一样,吓得直摆手,连连后退,“你的钱也是血汗钱,是用命换来的,我不能要。刚才的事,我就是做了个兄弟该做的。”
“拿着!”林冬把钱塞进大柱怀里,语气不容置疑,却充满了温情,“这不是给你的,是借给你的,也是入股。”
林冬指了指村后的那片荒山:“我知道你种地是把好手,养牲口也有一套。我想把村后的荒山包下来搞生态养殖,你来帮我管,这十万块算是启动资金。赚了咱们平分,赔了算我的。嫂子的病不能拖,得去大医院治,孩子的书也得好好读。”
王大柱看着林冬真诚的眼睛,那个七尺高的汉子,眼泪再也止不住,哗哗地往下流。他知道,林冬是在变着法地帮他,给他留足了尊严,也是在拉他一把,让他从泥潭里爬出来。
“行!冬子,我听你的!我一定好好干!要是干不好,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!”王大柱重重地点了点头,把那十万块钱紧紧抱在怀里。
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洒满了青石沟,给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镀上了一层金边。
林冬和王大柱坐在老屋的屋顶上,刚修好的瓦片在夕阳下泛着光。两人一人手里夹着根五块钱的红梅烟,吞云吐雾。
那个曾经装着两百万、引起全村轰动的破编织袋,已经被扔进了角落的垃圾堆,那是它最好的归宿。
林冬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皱皱巴巴的零钱,那是那天晚上王大柱砸了存钱罐凑给他的五百二十块三毛。
他把这些钱一张张展平,小心翼翼地收进钱包的最深处。
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,两百万或许能买来房子、车子,能让恶人低头,能让小人现形。但有些东西,是两百万买不到的。
比如这五百二十块里的情义,比如身边这个肯为你砸锅卖铁的兄弟,比如那颗在寒风中依然滚烫的心。
“冬子,这天看着明天是个好天啊。”王大柱吐出一口烟圈,看着远处火红的晚霞,眼里有了光。
“是啊,”林冬笑了,笑得无比踏实,无比舒心,“明天股票配资哪家好,肯定是个好天。”
发布于:河南省钱程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